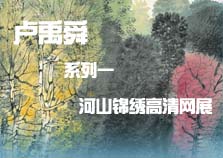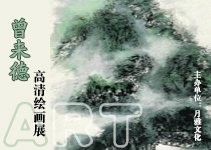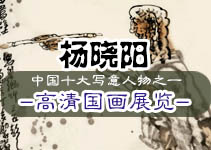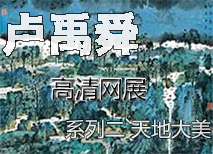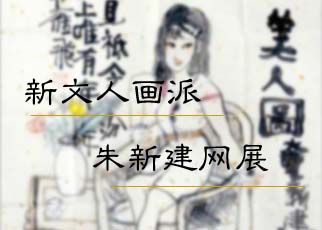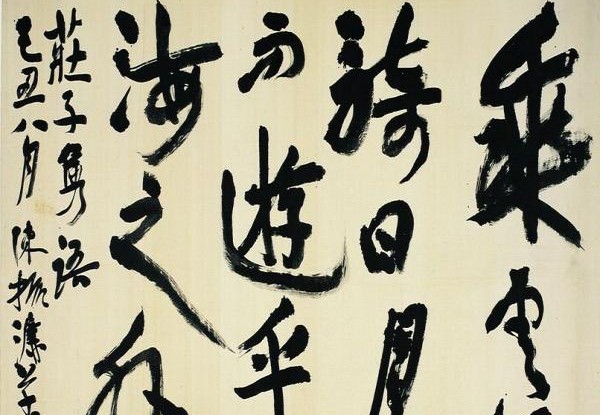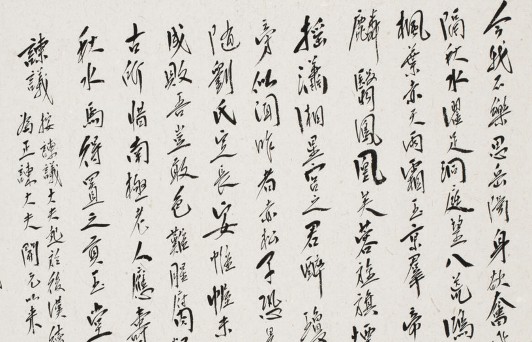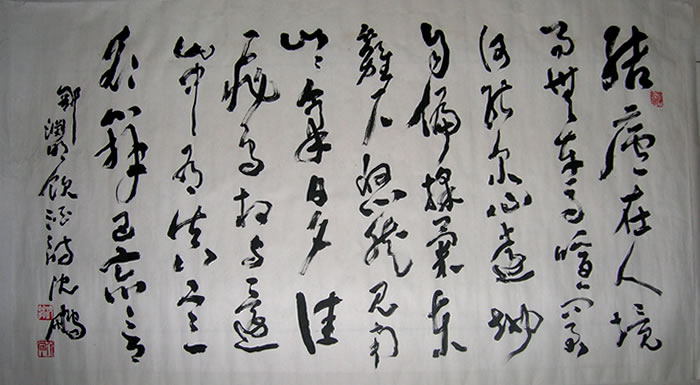书画界的“大师”现象 值得我们反思
2012-10-30
编辑 : 秩名
作者 : 未知
浏览次数 :
2005年6月30日,启功先生的逝世是书画界的一个重大损失,在全国引起木坏山崩的强烈地震式的反响,一时备极哀荣。启老是我所尊崇的一位前辈。早在1980年代,我参与王朝闻先生总主...
2005年6月30日,启功先生的逝世是书画界的一个重大损失,在全国引起木坏山崩的强烈地震式的反响,一时备极哀荣。启老是我所尊崇的一位前辈。早在1980年代,我参与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十二卷《中国美术史》,负责撰写清代书法部分,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对于帖学和馆阁体的评价。至少有100多年来,对此是持全盘否定意见的。我因早年得到谢稚柳和陈佩秋两位先生的点拨,所以对此并不盲目接受,而是作了客观的评价,在指出它的弊端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优长之处。当时负责审评我的文稿的正是启老,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见解。这一评价,有力地支持了我的信心,在嗣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,我反复倡导的晋唐宋元书画传统观,固然得力于谢、陈两位先生的教诲,同时也受益于启老的支持。但是,当我看到媒体上对启老的评价,推之为“国学大师”,却觉得很不是滋味。我想启老地下有知,也是决不敢承当这样高的评语的。
所谓“国学”,是指中国所固有的学术文化,这一概念大概形成于乾嘉学派整理国故之时。其具体的内容,则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。经部如《论语》等,是指从思想精神上规范全社会文化道德的学问;史部如《史记》等,是指从历史的借鉴来操作社会文化道德的学问;子部如《天工开物》等,是指从物质的层面来为社会文化道德提供基础的学问;集部如《杜工部集》等,是指文人士大夫个体情感抒发的学问。四部的关系是平行而不平等的,社会的大于个体的,所以集部居末;精神的大于物质的,所以子部居三;思想的又大于历史的,所以史部居次,而经部自然居首。书画艺术与冶炼、农业等百工的技术同属于子部,在国学中属于第三等的学问。
我们知道,在革命事业中,政治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活动,与农民种植水稻,都是革命事业所不可或缺的工作,但是,只有优秀的政治家才当得起“伟大革命家”的称誉,而再优秀的农民,也决不能称其为“伟大革命家”而只能是革命群众。这决不是贬低农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,而是革命的分工所决定的。同理,在国学事业中,只有在经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,如章太炎、马一浮等方当得起“国学大师”的称誉,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,一般也不被称作“国学大师”,至于在子部、集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工匠、艺术家、诗人、文人,更不可能被称之为“国学大师”。体育竞技中也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作为评价“体育强国”、“体育大国”的标志,它与“金牌大国”是两个概念。所以我想,根据启老所从事的行当,称之为“国学大师”是非常不妥的,这样的做法才是国学事业的重大损失!启老的学术贡献,称之为“书画大师”勉强可以及格。但具体而论,他的书法可以称之为“大家”,书画鉴定也可称之为“大家”,绘画只是位“名家”,诗词和声韵学的研究也只是“名家”。综合起来,客观地讲,是一位“大家”,放宽标准,不妨称为“大师”。严格地讲,“大师”不是像体育竞技的“冠军”那样,是针对今天书画界的现状,针对这一届比赛而言的。冠军是每一届比赛都有的,但能打破历届所创造世界纪录的冠军却并不是每一届都有。大家、名家也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的,但能够超越或者媲美前代大师成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师,却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段都有。所以,不仅从国学,就是从书画而言,尊崇启老是一回事,今天的时间段内他的成就远远超出同行是一回事,而把他称作“大师”,又是一回事。至于在诗词和声韵学方面,启老的成就是否超越或足以媲美夏承焘、王力等先生,也是大可商榷的。
什么是“大师”?记得好像是蔡元培先生说的:大学者,不是因为有大楼的缘故,而是因为其中有大师的缘故。大师,本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崇仰的学者而言,如《汉书》中讲到,“山东大师,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”。这里的巨大成就专指经学研究而言。后来扩充到其他领域,如在数学、史学等领域有巨大成就的学者,也被称为各自领域的大师。但至少到蔡元培的时代,艺术家的成就再巨大,一般也不称作大师,所以,当时的大学中,是很少有艺术系的,艺术有专门的艺术学院而不叫“艺术大学”。直到1950年代,齐白石、黄宾虹的最高称誉也是“人民艺术家”而不是“书画艺术大师”。但事实上,这两者的文化含量,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同等的,所以,后来,人们也把有巨大成就的艺术家称作“艺术大师”了。
总之,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近百年的学术文化史便可以发现,1950年代之前,各个学科的大师非常多,唯独书画艺术界,基本上没有大师。1950至1980年代,“大师”这个称号在各个学科都被废止了。而从1980年代至今,各个学科中都没有了大师,唯独书画艺术界,“大师”开始满天飞,甚至连一些年纪轻轻的书画家,也开始自封“大师”。从这一意义上,称启老为“书画大师”乃至“国学大师”,应该是当之无愧的。但“大师”不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能成立的。
书画界的“大师”成风,大概是由刘海粟先生在1980年代自封而启其端的,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,凡是去世的大家,活着的大家乃至名家,都成了“大师”。
有一点我感到非常奇怪,比如说在造桥领域,今天的专家,成就明显超出了茅以升时代的专家,但造桥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位大师。两院院士的成就,在各自的学科中超越了前辈,至少媲美于前辈的,也有不少,但也没有一位大师。文、史、哲领域,同样也是如此,不仅没有国学大师,连经学大师、史学大师、哲学大师、文学大师也没有。包括演艺界,自梅兰芳、俞振飞之后,好像也不见一位艺术大师。而书画界,今天的书画家,其成就远远不及前代,却都纷纷成了“大师”,或自封,或他封。诚然,与同代人相比,他或许可以称为“大师”。但真正的大师,决不是就该学科同代人乃至同龄人比较的结果,而是就该学科历代人比较的结果。比如我是搞书法的,我够不够“书法大师”的资格,不是与活着的同代人相比,而是与历代人、至少是与近百年里的人相比,我的成就是不是超越了或足以媲美于右任、沈尹默、弘一、王蘧常……当然,对于连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的书家,即使这样的比较,也不会妨碍他自封“大师”的自信心。但即使如此,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,为什么造桥的专家,成就明明超越了茅以升时代的专家,而不自封或他封一两个“造桥大师”出来呢?
这里,便牵涉到书画界的专家与其他学科专家不同的文化修养问题。文化修养越高,便越会觉得“学问莫言我大于人,大于我者还多;境遇莫言我不如人,不如我者尚众”,所以自认为是“小材大用”,专业上、对社会的贡献上不要不知足,要不断提高,待遇上、对社会的索取上要知足,要常存感恩之心。文化修养越低,便越会觉得“学问我大于人,境遇我不如人”,所以自认为是“大材小用”,怀才不遇,专业上、对社会的贡献上知足了,待遇上、对社会的索取上永无止尽,所以要通过自封或他封“大师”,来停止专业上、对社会贡献上的不断提高,加大待遇上、对社会索取上的力度。
所谓“文化修养”,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。一是文化知识,二是文化素质。文、史、哲、诗,属于文化知识;做好本职工作、服务社会,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,达则兼济天下、穷则独善其身,属于文化素质。二者相较,文化素质对于一个书家文化修养的意义,尤大于文化知识。所谓“一个人的能力(文化知识)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(文化素质)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”,也即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。所以,有文化修养的书家,首先当然是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,又有高尚的文化素质;其次虽文化知识不够丰富,但却有高尚的文化素质。至于虽有丰富的文化知识,但文化素质低下,不肯做好本职工作,不愿服务社会,而是个人中心主义膨胀,达则得意忘形,穷则怨天尤人,那便成了“文人无行”,是决不能称之为有文化修养的。至于既无文化知识,或者不过一知半解,又无文化素质,因为是“书法家”了,所以自以为不得了,那就更谈不上文化修养了。
所谓“书法家”或者“画家”,意为书法或绘画这一领域的专家。在全国,书画领域的专家大概不会少于50万,凡是搞书画的,大概100人中至少有50人可以成为专家。但我想,全国搞物理的人,包括装电灯的,搞建筑、运输的,开汽车的,都属于物理这一学科的事情,大概不会少于1000万,但真正成为物理这一领域专家的“物理专家”,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万。可见,在其他领域,要想成为专家非常难,而在书画领域,要想成为专家太容易了。这样的现状,更促使了书画界的人,比之其他领域的人,文化素质更为低下。文化素质越高,就越是不会自封或他封“大师”;文化素质越低,就越是会自封或他封“大师”。这,正是为什么自1980年代以来,其他领域基本没有大师出现,而书画领域却“大师”满天飞的深层心理原因。
我平时接触到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,大多清贫寂寞地潜心于学术,其精神令人感动。所以尽管没有大师,但这些学科的成就,有的超越了前代,有的可以媲美于前代,即使有学术腐败,不及前代处,但至少与前代的距离还不至太远。而书画家们,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书画家们,大都夸夸其谈,急功近利,不择手段。所以尽管“大师”满天飞,但除了功力和才力的低下,贪欲和惰性的膨胀,远远超出了前代,论真正的艺术成就,相比于于右任、沈尹默、弘一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黄宾虹、张大千……却是一落千丈!
一言以蔽之,针对当前书画界的“大师”如云,书画的基本功,文化的知识,文化的素质,千头万绪,启老是当代的典范,但人们却视而不见,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?我想,首先要识得“羞耻”两字——子曰:“知耻近乎勇。”如果连“羞耻”两字也不识,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至于启老的逝世,所换来的是书画界的领域出了并失去了一位“国学大师”为自豪并惋惜,这实在不是对启老的尊崇,更不是书画界的福音,而恰恰是助长了书画界的恶风。试想,既然启老成了“国学大师”,那么,水涨船高,我们自己不是也就更有理由自封或他封为“大师”了吗?于兹,艺术上便没有了目标,欲求上更没有了止境。毫无疑问,给启老冠以“国学大师”的头衔者,主要是出于对启老的尊崇,再加上对什么是“国学”、什么是“大师”的常识不太了解。但这种做法,客观上会助长书画界自封或他封“大师”的风气变本加厉,导致书画艺术的停滞不前和书画家欲望的不断增长,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回到对启老一生成就的评价上来,结合其他学科的情况和书画界本身的情况,我觉得冠以“书画界的一代宗师”较为妥当。因为,正像冠军是每一届竞赛都有的,宗师也是每一代都有的,而世界纪录则并不是每一届竞赛都有的,它是超越届次的,同样,大师也不是每一代都有的,它是超越时代的。至于“国学的一代宗师”,目前有没有?我不清楚,而只知道国学界并没有封“师”的风气,至少,“国学的一代宗师”不太可能出现在书画界,更遑论“大师”。
如上所述,似乎对启老“不敬”,但根据“实事求是”和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的原则,我只能以这样的“不敬”来表达对启老的崇敬。而更重要和主要的,则是为了针砭书画界封“师”的不正之风。(作者:徐建融 来源:书法)
相关阅读
关键词 :
大师现象 反思 书画界
- 发表评论
-
-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>>
图文推荐
高清推荐
书画论坛热帖
国画论坛热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