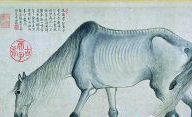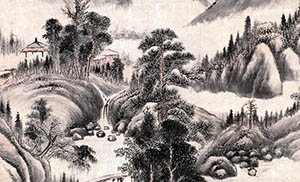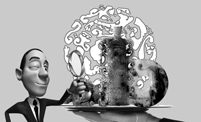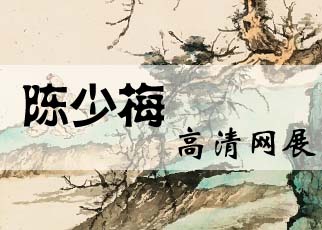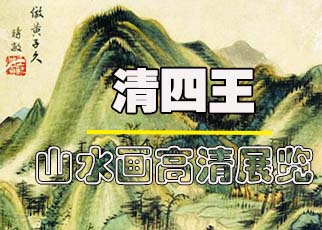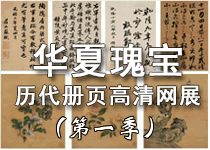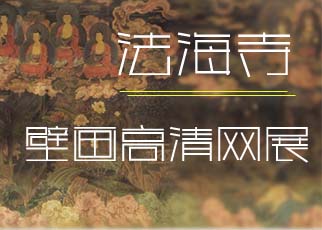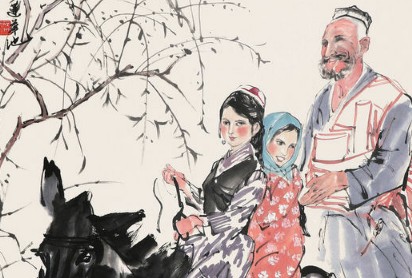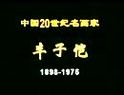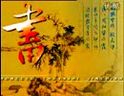当然其实还有着第三个原理,这是在摄影技术与绘画之间所打开的新视觉形式语言,从培根到里希特,超写实主义等等,都是把摄影视觉向绘画转换,非常经典的绘画,但也是非常当代的视觉感受。中国模仿里希特的艺术家异常之多。或者把绘画向着摄影转换,也企图寻找新的影像形式。
那么,如果“水墨”重要,应该也能够提取出一个原理出来,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呢?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核心问题。
当前争论的所谓“重要的是什么?”的问题,重要的是艺术吗?重要不是艺术吗?我觉得这个争论都不太清楚这样一个背景。其实杜尚也不是说完全不要艺术,我觉得1937年到1946年杜尚还是想回到架上,只是不大可能回得去,在西方不能把“艺术”和“非艺术”这两个东西重新连接在一起,杜尚和塞尚,这就是是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矛盾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做“虚薄”这个展览,试图面对这个杜尚与塞尚的两难,面对怎么做都不可以——怎么做都可以,的两难!
用水墨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吗?不是解决,而是试图来面对这个困难,使之更为富有弹性与张力,这是水墨的余地的问题,是水墨自身的余地与可能性,也是当代艺术本身的余地或者可能性,也就是从水墨中提取出出新的原理来面对这个两难!
水墨里面有一个原理一直没有被提取。中国水墨是一个混杂状态,既有官方水墨、礼品水墨,也有学院派水墨,也有实验水墨、抽象水墨、影像水墨,这些水墨在中国混杂在一起,都没有经过一个现代性的转换,没有经过像西方印象派、立体派、抽象主义这样一个严格的转换,所以水墨语言到底是什么样?是不清楚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水墨的原理提取出来,并普遍化,跟前面的两个原理一样的话,并且跟他们的两个原理相关,让西方人能够接受,那么我们就能做出来真正的贡献。
直接来说:水墨原理是什么?怎么去提取?我想直接首先有些冒然地说:中国传统文化水墨是一个“自然化”的原理,毛笔吸纳水与墨,水泼墨,墨泼水,水、墨、毛笔跟宣纸都是吸纳性的,这样一个“渗透”和“吸纳”的原理,“渗染”和“晕染”的原理,不仅仅是材质特性,其中还有某种自然化的原理,这是中国独有的。当然传统还主要是通过书写性的笔来实现的,这个更为具有个体性与生命气质变化的工夫!
这个原理跟西方的两个原理怎样发生关系?怎么实现它呢?
我们说西方的现代艺术明显通过几何学立体派做出贡献的,就是毕加索;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反这个方式的“非艺术”的方式,但是它也是现代性的方式。杜尚拿一个现成品的时候,恰恰是对物体的“物性”、独一无二的“物性”的尊重,这个“物性”拓展了它的功能,拓了已有的空间,摆脱了它的属性,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个体意识,这个个体意识是没有固定的,我给它什么属性它就是什么属性,就是一种自由经验;几何面的提取也是一个自由经验,就说我不是附着在一个具体形状上,我要把这个几何形提取出来——这两者都是一个“自由”的提取。而我觉得20世纪中国艺术还没有经历如此“自由化”的经验,这个经验还不够,所以我们需要转化。那么水墨在传统画里面,也跟对象(比如跟自然山水、跟材质)有一种固定关系,那么它怎么定义“自由”的现代性转化呢?我这个是最关键的。
所谓水墨的“自然化”,就是“吸纳性”的原理,毛笔蘸墨,是吸水、吸墨,水泼墨,墨泼水,毛笔蘸过以后,在宣纸上是吃进去的,宣纸有一种吸纳的功能;从材料一直到作画的方式,再到主体(一个写书法或者画山水画的人,写的不是字,不是线,而是气,是生命的气息),这是一个“吐纳”的原理——这个气息的“吐纳”跟“吸纳”是一个原理,中国传统山水的水墨材质、主体的气息跟外在自然对象的隐喻变化,这三者是共感的,都是一个吸纳性和吐纳性的原理,是对象——材质——主体,三者的共感,我敢说,西方艺术很难做到三者在生命上的共感!而大多是分裂的!这个三者共感,彼此渗透吸纳的原理,传统水墨对此了然于心,传统上是叫笔墨,它并不直接重视这个材质,而是更为强调笔性。
进入20世纪以后,说水墨而不是笔墨是在强调这个材质本身的吸纳性,而吸纳性、渗透性、渗染、润染这样一个自然化的“吸纳”语言是没有被20世纪充分利用的。赵无极的油画之所以是世界性的,就是因为把水墨语言以及山水画渗染的语言与油画,经过抽象化处理之后,生成出一个新的样式。实验水墨在做,但是都没有自觉,没有彻底做到像立体派、像杜尚那样以个人的名义,以自由的名义去转化,那么如果我们以个人自由的创作性想象,把这个自然原理转化出来,那么我们就把“自然”和“自由”结合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“吸纳性”展现出来,并且能够跟西方两个原理结合的话,那么我们就更博大了,当然除了这个自然的吸纳性的原理之外,还有一个原理,就是水墨的空无性。
- 发表评论
-
-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>>